
(報新聞/鄒志中 特稿) 近年來,「城市競爭力」這個詞不再只是GDP、招商或產業的代名詞。它逐漸轉化為一種更深層的文化能力——一座城市能否讓人願意留下、創造與感受。台中水湳經貿園區的公共藝術正是這場文化轉向的實驗場。從六年前開始籌劃、十五件的公共藝術作品、國際設計獎無數,到綠美圖、會展中心…等建設群聚的未來藍圖,台中正在嘗試一種結合「美學」與「經濟學」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。問題是,公共藝術真的能為台中這個城市帶來長期的競爭力嗎?還是僅止於一場短暫的形象工程?

從「造景」到「造勢」:藝術的經濟語言
台中「水湳經貿園區」的公共藝術案以「低碳、智慧、環境共生」為理念,這組詞聽起來既環保又科技,但它背後其實是一種城市品牌策略。公共藝術不只是裝飾空間,它是都市再開發的話語之一,是「讓土地升值」的軟性力量。這點從文化局的說法可見一斑——藝術不僅美化環境,更要呼應綠色城市的永續精神,形成一條文化經濟廊帶。
這樣的策略與全球趨勢相符。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落成後,南岸地區的房價上升逾30%;西班牙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帶來「畢爾包效應」,成為城市再生的代名詞。公共藝術若能與地方經濟結構連結,確實可能轉化為具體的經濟成果。然而,當藝術成為投資語言的一部分,它也面臨一個兩難:當藝術成為「價值創造」的工具,它還能維持其原本的公共性嗎?

藝術與空間共構:水湳城市敘事
「水湳機場」原為軍民合用機場,歷經轉型,如今變身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亮點之一。「水湳經貿園區」公共藝術策展人陳惠婷指出,水湳中央公園被譽為「都市之肺」,藝術作品則是這片綠肺的「脈搏」。這句話,雖然詩意,但也是策略性語言——它試圖用美學敘事重構台中市民對土地的情感。
例如紐西蘭藝術家菲爾‧普瑞斯的《浮遊之花》,以台中市花山櫻花為靈感,隨風而動;郭國相的《綠野遊蹤》以毛毛蟲造型橫臥草地,象徵生命與環境的共生。這些作品不僅吸引打卡人潮,更重要的是,它們在重建「地方記憶」。在AR作品《我在水湳的故事》中,台中市民透過手機看到昔日「水湳機場」的景象,彷彿參與一場穿越——那是歷史的覆寫,也是情感的回收。
城市學者沙斯基亞‧薩森曾說:「全球化時代,地方性反而成為城市最稀缺的資本。」「水湳經貿園區」的公共藝術正是在全球語彙下重建地方敘事。它將「去工業化」的舊空間,轉譯為「文化創新」的新資產。

榮耀與風險:當藝術進入政策體系
「水湳經貿園區」的15件公共藝術屢獲國際設計獎,包括繆思設計獎、法國設計獎、瑞士建築設計獎…等,這些獎項在台中市文化經濟上確實提升城市能見度。然而,從經濟學角度來看,獎項的「曝光價值」並不等同於「生產力」。藝術的價值若過度依附於外部評價,城市政策就可能陷入「表演性陷阱」——為了獲獎而造景,為了城市形象而投資。
這種情況並非台中獨有。東京奧運後,許多臨時性文化設施被閒置;新加坡濱海灣的藝術裝置,部分因維護成本過高而被拆除。公共藝術若無持續的社區參與與維護機制,其生命週期往往短暫。經濟學上稱之為「文化資本折舊」——看似一次性投資,實則需要長期管理。
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曾能汀副局長提出「低碳、智慧、環境共生」三大主軸,這其實是一種ESG導向的文化政策。它將藝術納入城市永續指標,但若沒有明確的經濟回饋或社會評估機制,公共藝術恐怕難以在財政與文化之間找到平衡。

文化投資乘數效應:美學與經濟共生
在經濟學上,文化投資被視為一種「外部性資產」。根據OECD的估算,城市文化投資每增加1美元,能帶動1.6至2.4美元的地方經濟活動,包括觀光、餐飲、創意產業…等。台中水湳若能藉由公共藝術導入跨界創新,例如結合AR導覽、地方創業、藝文教育,便能形成真正的乘數效應。
但若僅停留在「賞心悅目」的層次,公共藝術就會被邊緣化為城市的裝飾品。以《綠野遊蹤》為例,毛毛蟲造型可愛親民,但若無配套的教育或社區互動,它就只是「可拍照的藝術」,而非「可對話的文化」。真正具競爭力的城市藝術,應能引發居民思考自身與城市的關係,而非僅僅提供一個拍照背景。

從「公共藝術」到「公共經濟」:城市的下一步
公共藝術的意義,不只是「公共空間中的藝術」,而是「以公共方式運作的藝術」。這意味著它應該讓市民有參與的權利、創造的空間與反思的自由。當公共藝術能促使台中市民重新理解城市,城市的「軟實力」才會轉化為真正的「硬競爭力」。
「水湳經貿園區」的轉型提供了一個啟示:城市競爭力不僅來自基礎建設的速度,更來自文化結構的深度。若台中市政府能將公共藝術納入長期都市策略,建立維護與再利用的制度(例如:公共藝術信託基金),那麼藝術將不再只是「點狀風景」,而會成為推動城市持續成長的「結構力量」。
畢竟,城市競爭力的終極考驗,不是建了多少棟建築、拿了多少國際獎項,而是——這些投資是否讓人更願意在此生活、創業與創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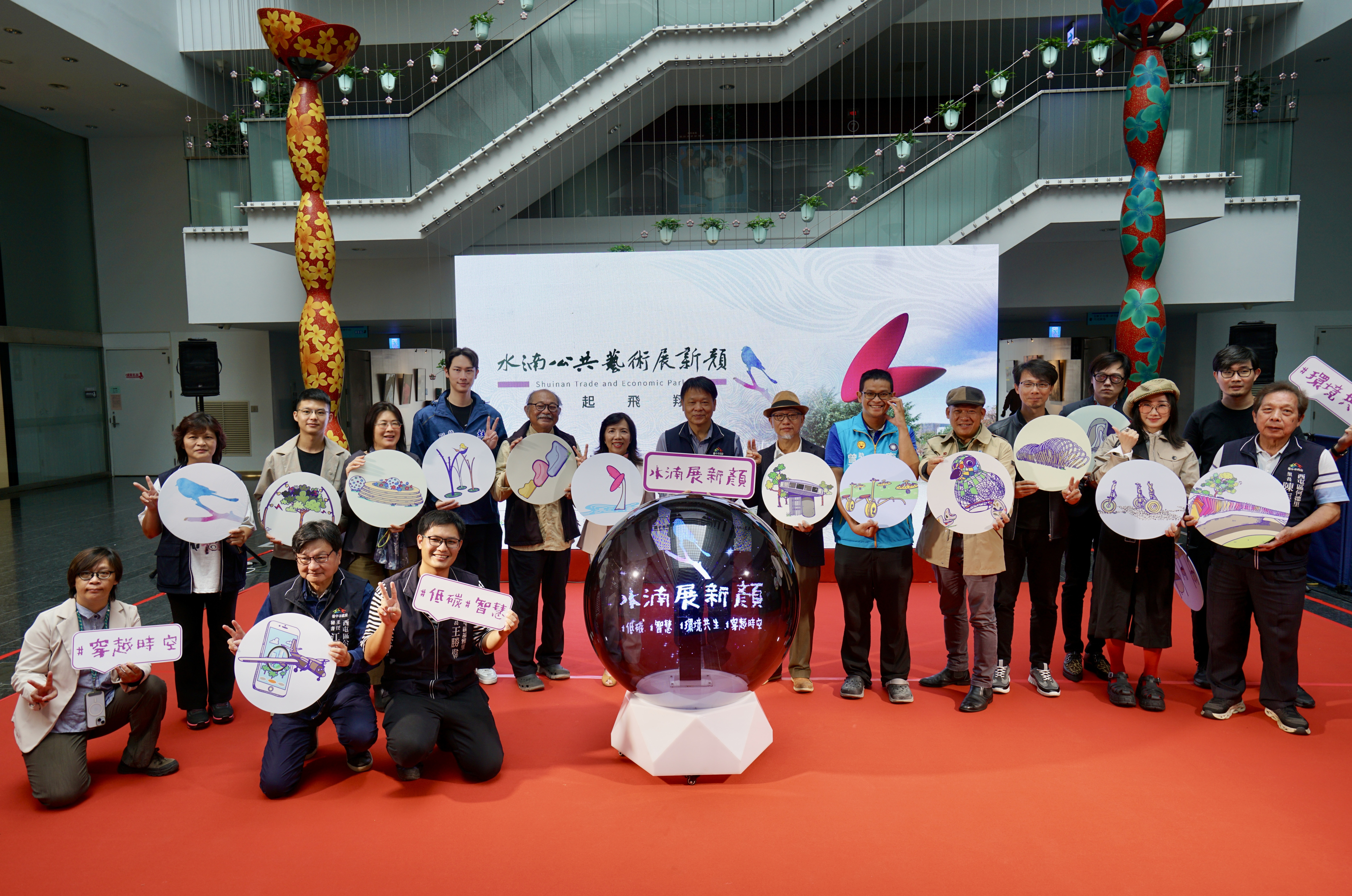
城市美學的真正價值
台中市「水湳經貿園區」的公共藝術無疑是一場成功的開端。它讓台中不只是「有建設的城市」,更成為「懂得講故事的城市」。然而,美學不是結局,它只是起點。若台中城市治理者能理解藝術不僅是文化投資,更是經濟體質的調整工具,那麼台中的未來競爭力將建立在一個更深的基礎上——讓文化與經濟相互滲透,讓台中的城市發展不再只是數字的成長,而是生活品質的提升。
城市的真正競爭力,或許就藏在那些會隨風擺動的《浮遊之花》裡。當藝術與土地、記憶與未來能夠共生,台中這座城市才算真正的活著。

